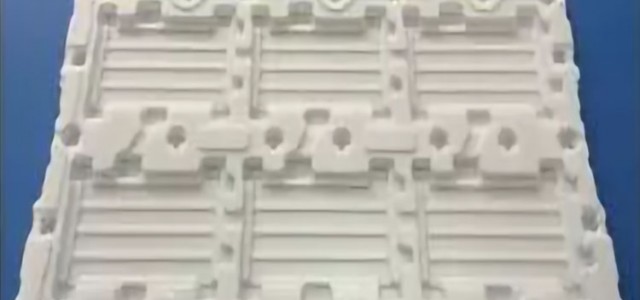長三角一體化進程中,今天的上海,比以往任何一個時候都顯得更加開放。最直觀的表現就是:那些居住在上海周邊城市的人們,甚至感覺不到自己有哪一刻離開過上海
本報記者 杜晨薇
今天,有超過5萬人每天往來于上海和蘇州,上班,回家。如果再算上那些為了節約時間選擇偶爾或周末往返的,這個數字還要龐大。他們,如同一群候鳥,平均100公里以上的通勤距離、平均90分鐘以上的單程通勤時間,抵擋不住5萬個為前途奔忙的人,也抵擋不住5萬個奮力團圓的家。
在上海同濟大學、英國利物浦大學等多所高校教授眼中,這群“候鳥”,構成了研究長三角一體化、研究高鐵規劃時,無比特殊而又重要的樣本。然而,他們的遷徙故事,只能在冰冷的數據里讀到,就連他們的身邊人也很少試著理解,為什么他們寧肯把生命里將近六分之一的時間花費在路上,也割舍不掉對其中任何一座城市的眷戀?
我們試圖回答這個問題。
通勤者數量達5.7萬
三年了,盧平(化名)每個工作日都要坐兩次火車。
火車,確切地說是高鐵。但人們習慣說前者,因為這透著一種長途跋涉、千山萬水之感。“天吶,你竟然坐火車上下班。”這是周圍人對盧平最大的不解。
早上6點40分,預約的出租車會準時開到盧平家樓下,終點是蘇州火車站,或蘇州園區站。具體就取決于他前一天買到了哪一站的火車票。高鐵運行半小時后,盧平已經身處另一個城市,上海。
他比車上的大多數旅客要從容,因為這條線路之于他,熟悉得像家門口的某路公共汽車。但他又比大多數旅客焦慮,因為他必須在停車的一剎那第一個沖出艙門,趕前往陸家嘴的地鐵。110分鐘,是他留給這趟旅程的最大時間額度,超過了,便會面臨上班遲到風險。
只知道盧平從事金融行業,但具體在哪一幢樓,哪一層的哪一家公司,不得而知。盧平要隱去的,是自己跨越蘇滬通勤這件事。盧平自然有他的道理。跨城通勤這件事,往往會留給老板一個刻板印象——“你不能加班以及勝任繁重工作”。
因此,盧平不僅對他的通勤狀態諱莫如深,還要把自己的通勤經過分割成不同“標段”,不斷優化,嚴格執行:打車到蘇州站或蘇州工業園區站,平均狀態下,前者會比后者少花10分鐘,但前者因進站流程煩瑣,走上高鐵要比后者多花12分鐘,而后者因距離上海更近,大概率會提前5分鐘到達……根據每天出行的實際情況,盧平會不斷對自己的線路進行排列組合,以保證全年的遲到次數能控制在5以內。
而對于那些加班已成常態的行業,跨城通勤者要克服的,遠遠不止“隱”這件事。2019年一個冬夜,9點,上海下起了雨。剛剛結束加班的程序員呂力偉在一個叫作“蘇滬鐵道游擊隊”的微信群里,發了一則酒店的優惠鏈接,就是只要有人點擊,就可以幫他領優惠券的那種。群里的人對這樣的信息大概已經司空見慣,半天無人回復。是啊,一年中誰沒有過累成這樣的時候,連回家的力氣也沒有。呂力偉有一家固定去的酒店:“我很認床,換了地方很難入睡,這里就當第二個家了。”
很多長三角地區跨城通勤者,都會加入一個甚至多個這樣的群。群里,少則幾十號人,多則三四百號人,談論最多的話題是搶票、酒店、拼車。
這是一個特殊的圈子。他們多數會把自己在群里的名字改成“某某-某地-某地”,比如“Gray-蘇州園區-楊浦”。主要是為了形成互助關系,順路的人可以快速鎖定一個旅伴。更大的價值在于它提供了心理慰藉。原來這么多人在跨城上班。公司在漕河涇的,看到公司在楊浦的,還會偷著樂。“至少比對方少坐一小時地鐵。”
而真實的圈子,則遠比通勤者們想象的大得多。過去兩年間,上海同濟大學建筑與城市規劃學院教授鈕心毅帶著團隊采集了上海與周邊城市(包括江蘇省南京、蘇州、無錫、常州、鎮江、揚州、泰州、南通8個地級市,浙江省杭州、寧波、湖州、嘉興、紹興、舟山、臺州7個地級市)所有的中國聯通匿名手機信令數據,共識別到2000多萬常住地用戶。研究認為,實際生活中每日來滬工作的長三角通勤者數量已經達到5.7萬余人,其中,蘇州與上海的通勤聯系最強,占到所有跨城通勤量的88%。而所有在上海中心城區工作的跨城通勤者中,有97%來自蘇州。
在長三角,你從來不是一個人在戰斗。
對時間敏感、崗位關鍵
在一個城市生活,去另一個城市上班,并不是多罕見的事。尤其在城與城的邊界,人自然地發生流動,行政區隔并不會成為障礙。然而,頻繁地從一個城市的中心,去到另一座城市的中心,卻有些特殊。“在國內,恐怕只有蘇州和上海是這樣了。”鈕心毅認為,這些日常往來蘇滬的人們,是在區域一體化課題下具有研究價值的、真正意義上的跨城通勤者。
英國利物浦大學地理與規劃系助理教授陳嘉琳曾用一年時間,研究那些在蘇滬高鐵線路上長期通勤的人,包括他們的家庭、工作、個人發展現狀,得到288個有價值的樣本。研究證實,大多數長期跨城通勤的人,對時間格外敏感。換句話說,他們比大多數人更看重時間的意義。
人們會利用每天在高鐵上的時間,回復電子郵件,或完成一些案頭工作。有受訪者告訴陳嘉琳,為了不占用回家后的時間,他甚至會把理發這樣的生活瑣事安排在工作日的午休。還有人選擇一回家就關機,斷絕一切與工作相關的聯系,是跨城通勤,讓他更珍惜和家人在一起的時間。而如果你問呂力偉,他會告訴你:“我雖然把大量時間花在路上,但并沒有浪費。我會在車上看書,刷微博和新聞。”——他們以實際行動,抵抗著因通勤帶來的時間消耗,讓路上的每一分鐘值回票價。
人們還會“精心”設計自己從居住地到工作地的路線,以便盡最大可能節約時間。陳嘉琳發現,大多數受訪者會把房子買在火車站的周邊。鈕心毅更進一步用大數據分析驗證了這一點:絕大部分來自蘇州的通勤者,會把居住地選在蘇州站或蘇州工業園區站30分鐘的時間距離范圍內。而他們的工作地,91%分布在上海市域內地鐵站1.5公里范圍。因為距離,直接關乎成本。
盧平每月花在通勤上的錢,大致相當于在上海的近郊租一套40平方米的房子,3000到4000元。因為不愿讓公司知道他跨城通勤這件事,他從沒去申請過報銷。事實上,在陳嘉琳的研究中,60%的通勤者都是在沒有公司支持下,獨立承擔旅費的。“什么樣的人能承擔起這樣的通勤成本?顯然,他至少不會是一個普通崗位上的普通職工。否則,他大可以在家門口找到合適的工作,省下這筆費用。”鈕心毅認為,一個人愿意負擔的成本,與他創造價值的能力密切相關。“我猜想,愿意跨城通勤的人,至少處在一個關鍵崗位上。”
今年,鈕心毅特地在研究中加入了百度提供的用戶畫像,發現從蘇州、昆山、太倉等多地進入上海的通勤者中,超過三分之一的人,月收入達到9000元及以上。尤其是從蘇州工業園區站進入上海的,月收入超9000元者為54%。陳嘉琳獲得的結論更具體,在她調研過的288個通勤者中,44.64%月薪超過2萬,超過38%的人,月薪在1到2萬之間。而他們的崗位,也大都處于管理層:25%是公司的主管或經理,超過41%是公司的高技術人員或專家型人員(如會計師、律師等),23%是業務經理。
然而,跨城通勤的成本遠比想象得更大、更復雜。陳嘉琳深入分析了通勤者在乘坐高鐵通勤前后,身心健康發生了何種變化。她發現,人們對跨城通勤這件事,是存在普遍焦慮的,主要的心理負擔來自“搶票”。從蘇州開往上海的列車早高峰時段最密集,但這并不意味著便利。通勤者往往需要提前一天,去購票軟件購票。遇上災害天氣或寒暑假時,購票的競爭會變得激烈。
當然,萬一買不到票,他們亦有解決的辦法,比如買到終點的前一站,上車后再補票。又如買當天其他班次的列車,再“混上”你所想要乘坐的班次。
這時,車站工作人員會是他們最好的助攻,哪怕票對不上,還是會放人進去——實在是因為往來通勤的人太多了,誰會去為難一個為前途奔波的旅人呢?車站寧可打破“規則”,為他們行個方便。可即便如此,長期“搶票”以及與之相關的種種行為,仍足夠碾壓一個跨城通勤者的心力。
“職住平衡”空間大了
他們為什么要跨越100公里去上班?
跨越蘇滬兩地的生活,周楊和家人一起過了5年。5年間,周楊工作日在上海租房,周末回蘇州和家人團聚,而妻子則不得不扛起照顧家庭的大部分重任。
周楊幾次設法結束這種兩地分居的情形,“主要是不想讓她太辛苦。”但反復論證的結果是,沒有比維持現狀更優的選擇了。
周楊和妻子是蘇州大學的同窗,妻子也是蘇州人,大部分的社會關系已在蘇州扎根。如果要舉家搬遷到上海,損失更大。周楊必須做出選擇:要不要離開上海,在蘇州找一份同等“價值”的工作,一家人或者就可以結束這種外人眼中動蕩不安的雙城生活。
然而,這其實是一條不切實際的“死胡同”。周楊在陸家嘴一家醫療企業擔任華東區大區經理。因行業特性,企業幾乎所有關聯方和業務重心都在上海。要想在蘇州找到同等職位、薪資水平、發展前景的崗位,幾乎不可能。周楊的人生價值,注定要和上海這座城市捆綁在一起。
事實上,幾乎每個家庭作出跨城通勤的決定,都不是盲目的,而是基于充分的評估和權衡——不是他們不在乎付出如此大的成本,而是在測算成本與收益的過程中,雙城生活,已然代表著利益最大化。更或者,根本就是外人的邏輯起點錯了:我們總以為那些選擇跨城上班的人們,是做了帶著悲情色彩的無奈選擇,而忽略了,在長三角一體化的進程中,人力資源在以不可阻擋之勢自由流動著,這是市場的選擇。
“工作在紐約,居住在新澤西,很正常啊!”上海前灘新興產業研究院院長何萬篷如是說。在他眼里,跨城流動是一種典型的分工現象。“有人覺得職住平衡才好(即居住地和工作地的距離合適),似乎跨城就不平衡了,不好了。但平衡實際上是相對的,在區域一體化的趨勢下,人們的交通方式和工作方式都在發生變革,‘平衡’的空間范圍是可以不斷擴大的。”
而在歐洲,這種“大范圍平衡”早已被人為地塑造而成。在法國巴黎,隨著服務業的不斷分化,只有高端服務業留在城市中心,常規的服務行業則不斷向城市外圍疏解,以商務通行為功能設計的高鐵,也自然地承擔起了跨城通勤的職能。這是區域勞動力市場一體化配置的必然結果。
而在上海、蘇州等更多長三角城市所組成的區域空間里,這種差異化的功能配置也在不斷凸顯。陳嘉琳調研的通勤樣本中,從事制造業的通勤者占比最高,近總數的四分之一,第二位是咨詢和IT類,第三位是金融類。“你可以從中看出,為什么他們可以住在蘇州或任何地方,卻只能去上海工作。”制造業,絕大多數高端制造行業的總部,會設置在上海;咨詢等高端服務業,頂尖的、全球知名的機構都在上海集聚;金融業,更是如此。“蘇州從2005年到2015年十年間,金融領域幾乎沒有優質的增量。”而上海則是面向國際的金融中心。
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在鈕心毅的大數據研究中,這些從蘇州進入上海的通勤者,最主要的工作地點都落在了陸家嘴、人民廣場、漕河涇、臨空經濟園區、張江園區等地——它們是上海高端服務業、高新技術產業的集聚地。
是市場決定了流動,并在流動中分化出了不同城市的核心價值:蘇州的確有它獨特的宜居魅力,但上海獨具對高端產業要素的吸引力。
直達更深層次一體化
今天的上海,比以往任何一個時候,都顯得更加開放。最直觀的表現就是:那些居住在上海周邊城市的人們,甚至感覺不到自己有哪一刻離開過上海。
鈕心毅的朋友,一位在上海東北部一所高校就職的教授,將房子買在了毗鄰上海西北角的昆山市。隨著連接兩城的地鐵11號線開通,通勤變得輕而易舉。他只需換乘一次地鐵,一個多小時,就可以到達工作地。他從不覺得自己住在上海之外。城市溢出的溫度,在長三角一體化的實踐中,將城市與城市、地區與地區間彌合得幾乎看不到邊界。
年初,盧平在靠近上海虹橋火車站的區域,買了一套屬于自己的小房子。但這不意味著,他決定就此結束眼下的雙城生活。房子是他真正成為“上海人”的外在標志,但他也認可,自己作為“蘇州人”的身份。他喜歡這種兩地都有家,兩地都能找到歸屬的感覺。
“我感覺,我是兩個城市的主人,我可以吸收兩座城市的精華。上海給我好的發展機會,讓我享受一流的文化設施。蘇州能保證我擁有節奏不那么快的、閑適的生活狀態。別人以為我兩地跑是‘受罪’,我卻覺得這是占盡兩座城市的優勢資源。”更大的收獲在于,盧平交到了兩座城市里的朋友,擁有了兩張密織的社會網絡。
因有長期在海外生活或工作的經歷,周楊對“雙城生活”的態度更灑脫些。“為什么要談認同呢,國外很多人都不認為自己是某個城市的人,他們只是生活在某個共同的城市圈。”周楊說,他是貴州人,在蘇州、上海,都不需要確立身份認同,“這不妨礙我去享受這兩座城市各具特色的氛圍。”
長三角一體化,至少面臨多個層次的努力:最低層次是形態一體化,比如交通基礎設施的聯通;中間一層是功能一體化;再上一層是治理一體化,需要打通體制機制。鈕心毅說,“只有當最低層次的一體化按照規劃標準落地實施了,才能從下往上,逐步推動后兩個層次一體化的實現。”而跨越蘇州和上海的通勤者們,卻用一次次不畏路遠的往來,直達更深層次的一體化:認同一體化。
同是長三角人,不論來處,不問歸處。